Raisa 不早也不遲,九點正在房門口示意早餐已準備好。陽光斜落在白色的檯布上,桌上除了我的用餐碟外,還有很多小配碟,盛有牛油、小牛奶瓶、木瓜、葡萄、雪梨、椑梨、果醬、芝士、當然還有地道特產的乾辣香腸片,鋪陳得極為細緻。吃過早餐,臨出門時我問 Artush 是否適宜穿短褲出外,他飾如一位恰如其份提供地方背景資料的導遊一樣,說久姆里地處一千五百米的高地上,晚上會比較清寒。
從 Artush 家出發,天氣有點涼,清風吹過,令人精神煥發。經過一間學校,旁邊有十來個學生正進行短跑比賽,二人一組,老師在終點旁計時。再過不遠處,有位婆婆打掃在地上的落葉。再往前行是一個大迴旋處,有一個高高的鮭紅色拱門,拱門前是一個銅像。迴旋處向右拐是寬闊的 Garegin Nzhdeh 大馬路,一直向南通往巿中心。心裡突然喚起 In the morning 這首歌,我想是潛意識裡接通了其中一句歌詞 —— 'tis the morning of my life ....
一路經過了一座酒店、四層高的巿政府大廈、警察辦公室、一些路旁的小賣亭。心裡想著:亞美尼亞,亞美尼亞。這個小國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字母有三十六個),這個國家與鄰國交惡,東邊有亞塞拜疆,西邊有土耳其,不問因由,好容易產生一個印象:這個國家是好挑事份子,但又有哪個國家可以好像亞美尼亞一樣,同時和美國、俄羅斯、伊朗交好?思想玩味在國家間的紛爭上並沒有絲毫減退我當時愉悅的感覺。
我先到了一座名叫 Surp Nishan Church 的細小教堂。有兩個年青人經過,向教堂的門外石壁親吻,之後又有一位少女走進教堂站在祭壇前,劃上了十字後在祈禱。這教堂雖細小,但簡單別緻,入口通道掛有聖像油畫,陽光透過油彩窗口,顯現出美麗宗教畫像。
我雖踏足了亞美尼亞已超過一星期,但之前參觀過的教堂都屬歷史古蹟,在頭腦上所產生的意識,可能和我在廣州從熙來攘往的閙市中遠望石室聖心教堂差不多,找不到與現時當地人生活的相關痕跡。直至方才這幾個人帶有宗教性的行為,我才真正意會到這個事實,就是這個位於高加索與伊朗為隣的國家,人民普遍仍然信奉着承傳下來的基督教。
沿著由石塊砌成的路徑向上一路是民居,兩層高,整體頗有特色,偶然踫上一些屋址磚石散落,應是1988年那次發生在久姆里的大地震造成的,當時造成五萬人死亡,市內大部分地方被移為平地。之後到了大廣場,廣場旁分別有巿政廳、Yot Verk Church、和仍在修建中的 The Holy Savior Cathedral。Artush 曾提及過由於政府財困緣故,地震後至今二十多年教堂仍在修建,但預計明年會完成工程。
之後我步行到城東邊的火車站,想訂兩天後前往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的通宵火車車票。車站大堂內空無一人,售票員不懂英語,只好靠電話中懂英語的第三者充當中間人溝通。原以為由久姆里往第比利斯的火車開出時間是凌晨,但經過多翻將手提電話互相傳交,我才從售票員得知開出的時間是下午五點二十分,到達目的地的時間將會是夜深,極為不便,於是決定將改為乘小型公車前往。
離開火車站往西邊折返,經過平民區,有一老伯在門外用斧頭伐木,地上堆滿大小不同的木頭。他向我揮手,又招呼我入屋內。起初他領我到他擺放木材的房間坐下,然後準備咖啡,後來住在他隔鄰的兄長來到,兄長又帶我到他的屋內參觀。兩兄弟和我坐在小餐桌前喝咖啡;弟弟和我談話時,兄長不時將放在小碟子上五顏六色像小寶石粒般的糖拿出來,不以為意的擺在我的咖啡杯前。我說我從香港來,但不知怎樣他們說起噠賴喇嘛,於是我在紙上畫起中國的版圖,區分了西北方的西藏及南面一小點的香港。他們一個說:噢,Hong Kong,另一個說:Jackie Chan,此刻我知道成龍大哥的確是一位國際影星。
下午我到了城交處的亞美尼亞之母像,當時有一班學生在石像下幾百級的石級上跑上跑落做運動,有的在作兔跳一級級躍上去,又有兩個以雙手掌代腳倒立下石級。他們像是迫不得以,氣喘吁吁。我往北望,看到隔鄰山岡上有一座黑色堡壘,堡壘外的山邊上坐著一個男人。
我從亞美尼亞之母像旁邊的一條小徑通往那小山岡,山岡上這座名黑色堡壘的遺址叫 Sev Ghul。我從堡壘的一邊繞到另一面,眼下是山下整個久姆里市,巿內有很多高樹和矮樓房。我前面有一個男人獨坐在山邊,手中拿著一瓶啤酒。我站著外望山下巿鎮的景色,他察覺到我的存在,指著山下的景緻,然後豎起拇指。過了一陣,他轉眼望向我,示意我坐下,對我來說,這是有一種友善的邀請,一種想與別人分享自己覺得美麗的東西,於是我揀了距離他大概四五米處坐下休息。他不懂英語,我們作了很簡單的交談。我已記不起是什麼緣由,我們最後一起並排而坐,望向山下。他向我遞上他手中的那瓶啤酒,我微笑搖頭拒絕,他又給我香煙,我也拒絕。沈默了一會後,他指著右方遠處,然後兩前臂交差放在胸口上,做了一個象徵珍愛的手勢。我以為他的意思是他的愛人住在那方,所以我在拍字簿上畫了一個火柴枝女孩,旁邊加上心形。他拿了我的拍字簿,另外畫上了一個十字架,我猶豫著,不知應怎樣猜想及回應時,Artyr 已眼眨淚光,目光稍離我移開,深呼吸忍著淚水,再用右手手心在眼窩處抹掉眼淚,他肩膊微微抖震。我將手在他背上輕拍了幾下,他說 papa,mama。
之後我們都望著前面遠方的景色,說的話不多。他站起身,邀請我到他家裡,我們起程前,他給我一粒口香糖,這次我沒有拒絕。
Artyr 的家距離堡壘大概十五分鐘步行路程的一條小村莊。村口靠大馬路,有一間雜貨店,然後是一兩層高的磚屋,大概過了十多座屋後向左拐入一些小巷,便到他家。當時屋裡有他的妻子、一對兒女、和岳父岳母。一進屋是一間窄長的房間,大概是三米乘八米,牆壁破舊,漆油多處脫落,由左起是一個電視機,一張長梳化椅,一張正方形餐桌和椅子,然後是雪櫃,最後是煮食用的地方。Artyr 向太太和岳父母介紹我,我續一向他們握手。然後他著我坐在方桌前,他坐在我身旁,又吩咐太太煮咖啡,奉上蜜瓜、葡萄。太太的動作例如抹檯面、擺刀叉、煲熱水等都很明顯十分很勤快,惟恐招呼不周,給我感覺到自己是他們的貴賓一樣。太太見到桌上剩下兩塊小西餅,連忙打開透明的盒子,一件給我,一件給她丈夫。
我在地圖上指出我在亞美尼亞的行程,他們夫婦都很感興趣,又建議我到其他比較受歡迎的旅遊勝地,如 Sevan、Tsaghkadzor。太太說她妺妺曾在葉里溫大學唸英語,還給她的畢業證書我看。我們談話間,他們七歳大的小女兒不時走到父親旁依偎,眼眯眯的,嘴唇兩邊微微向上,望著我們傾談,十分惹人喜愛,我曾經多次不由自主的凝視著這小女孩。我讚她長得漂亮,Artyr 打趣的表示這全歸功於他而不是他的太太。我們之後進入另一間比較寬敞的客廳,裡面有一張矮桌,三面圍繞著梳化椅,靠牆有高櫃,裡面擺放著一些茶具。我坐在梳化上,太太拿了兩張放在相架內兒女嬰兒時的舊照給我看,我想到與之相類似的城市版本——就是當你見到老友時,將你手機內的兒女照片分享給他們看。跟著太太又拿了女兒的英文課本給我,小妹妹站到我身邊,我翻開書本教導她書本內容,她慢慢續過音節讀出句子,「Whaaaat iiis yoooour naaame? My naaame iiis ... 」
Artyr 作了手勢叫我留在他們家裡過夜,在山上他也有同樣的邀請,但我沒有心理準備,所以拒絕了。現在回想起來,我很後悔沒有領情,讓我有機會多一點時間與這個友善的家庭相處。出外旅遊,大部分時間都是浮光掠影,而我在旅遊中,最嚮往的豈不是稍微了解當地普通人生活的點滴嗎?我很多時都為自己的怯懦懊悔。
Artyr 帶著兒女跟我到了附近的一個小公園,一路上我拖著妹妹的小手,她的衣服單薄,手有點冷,令人生發憐愛。
這個公園當中有一座教堂,而公園本身是用以紀念十九世紀俄羅斯軍人在附近參與與鄂圖曼戰爭而陣亡的士兵。之後 Artyr 到一個在附近雜貨店工作的朋友處,經幾番討價還價後終於借到他的汽車,說要送我回住處。我說不用,但想答謝他,建議找個地方喝杯咖啡或吃點東西。他做了一個姆指柔搓食指和中指的重複動作,雙肩向上,無奈的表示他沒有錢。我示意由我付賬,他不用擔心。於是他駕車到美術學院隔鄰的到一間西式餐廳。他替我們每人點了一客當地加上舖有蛋和芝士在上面的焗麵包,我將印有圖片的甜品餐單遞給兩姊弟,姐姐楝了一件粉紅色的士多啤梨蛋糕,而弟弟揀了一件忌廉蛋糕。
在餐廳門口道別過後,我目送 Artyr 駕車離去,依依不捨,像突然失落了些什麼似的,不能自已。我和他們萍水相逢,在很多巧合的條件下相處了一個下午;我不懂解釋我錯亂的思緒。
兩天後要過境前往第比利斯,所以特定預先前往公交車總站一趟。從車站返回民宿時,差不多七點,天色開始昏暗,清涼了很多。寬闊的路上不見人跡,碎紙在地上被風吹起旋轉飛舞,兩旁是破廢似的在建矮樓房和商店,電線桿之間缐路交錯,烏鴉在日落淡紅的上空飛過,呀呀作聲,點綴這刻絢麗的黃昏薄暮。我躊躇前行,想到今天遇見的人和事,彷彿觸摸到世界裡丁點兒的真實,心裡沈鬱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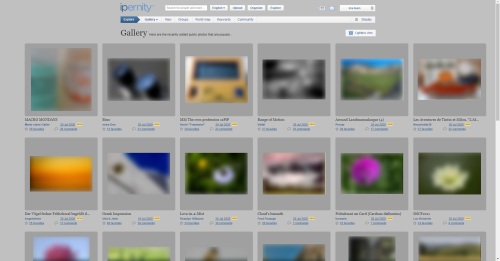
Sign-in to writ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