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ni, Geghard / 2012-09-06
Anna 寫下一張小字條給我,指示如何乘公交車從葉里溫到 Garni,她說她將會將字條上的文字輸入電腦,以便列印,以後不用再重複抄寫。
原本我要乘66號小巴到巿內一處寶馬汽車陣列室附近再轉乘巴士。在候車處一對老夫婦知我要到 Garni,老伯便一手拉我上10號巴士上,向司機說了些話,跟著又似乎向我解釋什麼,但礙於語言不通,老太太最後致電給她懂說英語的女兒,然後將電話給我,她女兒說父親已告知巴士司機讓我下車的車站,我也著她代我向老夫婦道謝。但最後司機並沒有通知我,可我憑 GPS 及事先在電子地圖定下的坐標,確定位置然後下車。
下了車後拐過路口,馬路對面便是前往 Garni 的巴士總站,站旁有幾個老人下著當地常見的棋子。我跳上車,揀了較前的雙座位,坐在窗邊處,將背包放在另一旁的座位上。我趁車還未開出,走到後方以便影下整個車廂,此時有一位大概五六十歳的長者上車,繞過我的背包,坐在我原本的座位上。我正取回背包準備到別個座位,他揮手示意叫我和他一起坐下。他是當地人,叫 Valery,是一個俄羅斯名字,情況類似香港人,除有自己中文名字外,通常也有英文名。Valery 從前是個飛機師,航行非洲大陸,包括蘇丹、埃及、利比亞,現在年紀開始老邁已退休,今天他乘車到 Garni 探朋友。在途中他談及在蘇丹有很多中國工人從事石油開採,而該國現時分成南、北蘇丹兩國,時而又在巴士經過的有利位置叫我影下遙遙相對的亞拉臘山。此山在二千年前已原屬於古亞美尼亞王國,其後隨著高加索地區不斷被不同民族爭奪,亞拉臘山亦先後被羅馬帝國、波斯帝國、鄂圖曼帝國佔領,而俄羅斯更在1923年與土耳其簽定條約將亞拉臘山劃入現今土耳其境內。這讓我想起中國的釣魚台問題,部分也是因美、日之間不涉及屬土國家的條約安排弄成至今的主權糾紛。Valery 說大概一百年前這山還屬於亞美尼亞的;的確亞美尼亞在1918年脫離鄂圖曼獨立取回阿拉臘山,但其後很快亞美尼亞便被蘇俄佔領。在車上,我們東拉西扯,說東說西,Valery 還說若非他事忙,他希望可陪我一起,作我嚮導。他感謝他的好意,同時心底裡覺得可惜,沒有機會和這位溫文和親的長者同遊。
藍天空,黃山群,天蒼野茫,巴士在柏油路上繼續前行,當中有這位老人和我。
到了 Garni,Valery 給我介紹了他的司機朋友 Ludvik,然後向我道別。我於是顧用了 Ludvik,乘他橙紅色的老舊 Lada 房車到 Geghard Monastery。我坐到他旁邊的前排座位,舖一坐下即塵土在陽光中紛飛,心想這架車在附近這兩個靠山的景區不知穿梭來回過多少次。沿路上幾次遇上有放羊的、放牛的,十來歲皮膚黝黑的牧童騎在馬上,眉目精悍。
之後汽車在公路飛馳,兩旁是貧瘠的石山,大概十五分鐘過後便到修道院。修道院於四世紀建成,九世紀被阿拉伯人焚毀,十二世紀由格魯吉亞王國下令復建,現時主教堂及西邊堂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下,與山坡緊嵌相連。修道院因曾收藏相傳曾用來刺穿在十字架上耶穌肋旁的芧而成為以往亞美尼亞基督徒的朝聖地方。穿過西邊的石拱門入口,面向西教堂及主教堂,北靠著山崕,另外三面被大概只有三米高的護城牆環圍。西教堂內由四條石柱支撐,上面半圓穹頂上有一個洞口讓陽光直透到教堂地上,西邊有多個石頭被鑿開而成的暗室。主教堂正門右邊擺放了兩個巨型宗教石牌,東邊山坡上有數個人工掘成作為修道的洞穴。
遊覽時還有其他外國遊客觀光,但人數不算多致卻步。逗留參觀一小時後,Ludvik 準時出現,催促我返回 Garni,後來我發現他想爭取時間以便載我到其他地方如 Sevan、Khor Virap,但我拒絕。
Garni Temple 是一座異教的神殿(所謂異教,只是從當地正統基督教的角度看),建築在高而幾乎垂直的山崖邊,下面是 Azat River,周圍是高山和峽谷,地勢險要。神殿是典型古希臘羅馬式建築,在我門外漢而言,與其他在希臘的神殿沒有多大分別,觀賞價值比不上方才遊覽過的 Geghard Monastery。遺址周圍豎起柱桿,掛上廣播器,播著類似奧林匹亞比賽開幕的音樂,為要營造氣氛。
步出 Garni Temple 至大路向右轉,準備前往附近的鄕村,途中在一所兒童音樂學校外停住定方位,學校裡的一個胖子揮手叫我入內,聽到我提及 Geghard,以為我需要找幫忙,說要幫我找的士,言語不通,他有他說,我有我說,最後他要打電話給他一位懂英語的朋友才弄過明白這是一塲誤會。原來這個胖子是 Garni 的鎮長。
再往前走,經過了一座小小的教堂 Holy Mother of God Church,看見兩個孩童在嬉戲,小徑對面不遠處有一位頭包格子花帕的老婆婆在屋外擺賣菜蔬,我從檯上揀了兩個鮮紅大番茄作解渴生津之用。進入村莊,周圍很寧靜,兩旁有青綠的矮樹和石磚鐵皮築成的小屋。下午三時的陽光和樹的影子落在沙石路上,光喑分明。心裡胡亂幻想著屋牆背後向可會有什麼家庭碎事發生:屋裡的人在閒著做什麼?一家人會不會在這時吃一些下午小食?吃的又是什麼?婆婆又會和孫女兒閒談些什麼?小孩又會有什麼古怪地度的玩意?
有一個農夫手拿著飼料和幾個半破開的西瓜,進入棚子裡餵雞。出於好奇,我上前想看看雞怎麼樣吃西瓜,這倒對牠們來說是不錯的消暑良品。農夫示意我在那裡等候,他進入旁邊的貯物小屋,安頓好東西,然後取來一隻雞蛋送給我,大概是剛剛產下的,雪白的外殻上有一小處印上乾了的血絲。他用手勢示意對面屬於他的石屋和破舊汽車,邀請我進入他屋外的陽台。兩層的石屋建於山坡上,陽台對著圍繞 Garni 的山脈,陽台下的山坡是農夫的小園地,種有桃子、梅子、黃瓜、蕃茄、青椒、靑蘋果、葡萄,又養蜜蜂採蜂蜜,還飼養了兩隻大兔子。
原本長桌子放在陽台對出處的一角,為避免日光照斜,這農夫 Arnak 將桌子搬入陽台,我座在蓋上藍布的沙發上,他對坐在長木櫈上,叫喊在屋內的妻子。妻子跟著將食物一碟一碟奉上,盡都是他們從地裡所出的蔬果、又有亞美尼亞人稱 lavash 的薄餅、芝士、牛油、蜜糖,又拿了一瓶干邑,但知我不飲酒,Arnat 叫妻子拿來了冰凍的梅子汁。他用各種的生果加芝士捲在薄餅裡,拿進屋內,大概是給妻子的,然後再出來和我共餐。
我們沒有共通語言,只能靠手勢動作溝通。Arnak 在我的紙巾上寫上51,然後指著自己,應該是指他的年紀,我指著他的妻子,他寫下48,然後我寫下我的年紀,他好像有點驚訝。我又用在幼稚園時學會到的火柴枝人畫了父親、母親、男孩子、女孩子。他表示有一兒一女,兒子去了俄羅斯(他後來拿了本地圖集給我看),女兒或許跑到了城市。
Arnak 帶我入屋內參觀,屋內陳設不是我想像的那樣簡陋,連廚房及廁所,屋內起碼有六個房了,面積比起絕大多數的香港家庭大得多。我對建築沒有認識,不知屋內為何沒有空調但那麼清涼。我們是從面向山的那道屋門進入,通過白色輕紗簾幕,先是廚房,內有白色靠牆的廚櫃和現代化煮食爐具(我之前還以為他們是燒柴的),再過一度門是一個小小的客廳,擺放著棗紅色皮梳化和一張長方形矮木茶几。客廳右邊是主人房,非常敞大,地上舖上中東色彩圖案的地毯,靠窗放了一張床、兩張獨立梳化椅和一部電視,相連的另一牆壁是一排長櫃,幾乎佔據整個牆壁,留下一小空間掛上一張油畫,畫中青綠的山崗上有兩間屋,一大一小,中間大的是 Arnak 這間屋,在旁小的是 Arnak 的鄰居。Arnak 示意這屋是他自己起建的,還在紙上寫著1991,於是我寫上21,他點頭,原來這間屋是 Arnak 在二十一年前建成的。我拍拍他的手臂,指著他,然後豎起大姆子,由衷的表示我對他的讚賞,他的表情略帶腼腆,但同時又挺自豪。
Arnak 帶我到山坡下他的園地,跟著又到小屋地下那層作為儲物用的地方,當中儲存著各類自製的酒類製品及醃製食品,都是用他園地種的蔬果製的,又向我展示屋內食水系統,我體會到這座他親手建成的屋子及每天耕作的園地就是他感到自豪的成就。
隔鄰的老婆婆來到與 Arnak 太太聊天,於是 Arnak 又帶我到隔鄰另一間屋介紹他的鄰居。其中一個大塊頭朋友要我替他們拍照,Arnak 很羞怯,十分不情願,又叫其他鄰居一起合照,好讓他比較沒有那麼尷尬,他最後還是屈就大塊頭朋友的糾纏拍下一張合照。一個能一手蓋建自己房子的男人,境在這小小的鏡頭前顯得不自在;我喜歡他的樸實。
出村莊的路徑經過一片墓地,家雞在沙地上啄食;Arnak 的屋子在我背後漸漸遠離。今天到過的地方、遇見過的人大概我以後也不會再踫上,感覺得很輕盈,生命彷彿沒有點實在,教人拭出眼淚。
美麗的落差
-
迪利然 (Dilijan) / 2012-09-07 ~ 10
是幾幅有幾分古城韻味的建築物相片?還是地理上鄰近幾個小鎮的原故?已記不清楚是什麼原因令我選上迪利然在我的行程當中。不過現在回看,在…
-
08 Sep 2012
亞美尼亞的梵蒂岡
-
艾奇米亞津 (Echmiadzin) / 2012-09-05
Anna 媽說她不會愚蠢到要跑到外國做二等公民,「為什麼我要到外國掃街!就算掃街我為什麼不在這裡掃!我才不信他們!(I don't…
-
05 Sep 2012
See all articles...
Keywords
Authorizations, license
-
Visible by: Everyone (public). -
All rights reserved
-
171 visits
Jump to top
RSS feed- Latest comments - Subscribe to the feed of comments related to this post
- ipernity © 2007-2024
- Help & Contact
|
Club news
|
About ipernity
|
History |
ipernity Club & Prices |
Guide of good conduct
Donate | Group guidelines | Privacy policy | Terms of use | Statutes | In memoria -
Facebook
Twi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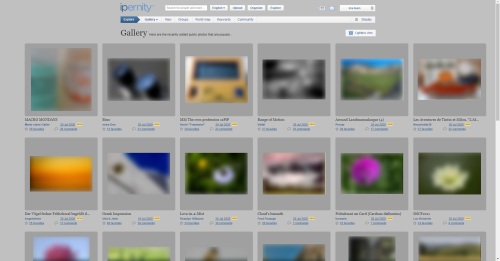
Sign-in to write a comment.